文章来源: 雨前产经观察/罗提 邱娟
不提供二次转载
身处中西部的城市,如何才能长出万亿级龙头企业?
这令很多地方政府辗转反侧,求而不得。
然而,一座“老、少、边、岛、贫”的三线城市做到了。2007年,这座当时连火车都没通的三线城市,与一家中小企业签订了投资建厂协议。
谁料,这家不起眼的企业后来竟生长出一个行业巨头,市值甚至一度超过中石油。
这座三线城市叫宁德,中小企业叫ATL,长出的龙头叫CATL——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的崛起在于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核心技术,而动力电池在大规模商用化后,制造产能也开始向中西部扩张,其中四川省就承接了多个项目。
2019年至今,宁德时代与宜宾陆续签订了六期项目,总投资超300亿。今年起,蜂巢能源投资71亿先在遂宁生产锂离子动力电池的电芯模组和电池包,又在成都东部新区简州新城投资220亿建动力电池制造和研发基地;璞泰来投资140亿在成都邛崃建设新能源电池材料全产业链项目;中航锂电也投资280亿在成都龙泉驿区建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成都基地。
这些项目诚然为四川就业、GDP与产业链集聚带来了好处,但在“尾雁紧随头雁”的雁行发展模式中,地方扮演的仍是尾雁追随角色,显然无法与宁德案例相比。
实际上,十几年前四川就承接过一波电子信息与汽车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富士康工厂从沿海转到成都、重庆、郑州多个中西部城市,成千上万的厂妹夜以继日在流水线上劳作。
历史似乎又在重演?
并不。这次不光有成熟产业的梯度转移,还有产业变革的新老交替。新兴产业的爆发正在为中西部城市孵化龙头企业留出机会。
瞄准种子,提前锁定企业
早期宁德引进ATL依然是梯度转移。
一开始公司创始人曾毓群只选择了在宁德建几个厂房,总部和主体仍留在东莞。后来宁德能反客为主,既得益于曾毓群的乡土情结,也与新能源的产业特点有关。
以往化石能源时代,能源具有强资源品属性。中东遍地是石油,山西产煤全靠开采,企业必须就近作业,不可能直接搬迁工厂。
而新能源的制造业属性远大于资源品属性,曾毓群建厂不用考虑当地是否有锂矿。且锂电池属于新兴产业,对区域、周边产业结构要求不高。
既然到哪建厂都差不多,何不回家乡?
ATL在宁德建厂后,管理和研发也陆续跟过来,一方面在于曾毓群的号召力和高薪吸引(宁德工资比东莞高30%),一方面在于锂电池的制造业特性。
锂电池的基础研发属于材料学,依赖实验对化学元素的不断组合试错,很难一夜突破,因此创新周期非常漫长。索尼1990年就发明了锂电池,直到前不久宁德时代才宣布在钠离子电池上重大突破,一晃三十多年。
在材料体系创新的大周期内,锂电池品质与能量密度的提升有赖工艺及经验改进。在宁德时代,工艺岗是要下产线的,工艺发生任何细微变化都会不可预测地改变产品特性,研发与制造的紧密程度越高,越有望实现创新突破。
当然,这只是初始工厂制造与研发高度结合。
当一项工艺成熟大规模商业化之后,宁德时代在其他地方扩建的工厂就是标准化生产了。
类似计算机、电子产品,行业工艺成熟度高,模块化生产程度高,制造与研发的分离度就高,联动关系就弱。
此外,宁德政府在人才引进上下了大力气,实行高级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一些专家甚至可以在当地享受到厅处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宁德时代员工的工资里面还有专门的政府补贴。
新兴产业的高端制造业属性,创始人的乡土情结,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决定了宁德招来第一个工厂后的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实现了梯度转移的逆袭。
这给人启示,地方政府要突破产业链招商的思维限制,深入研判新兴产业,瞄准种子企业,抢在其将扩大产能之际积极引进。
企业扩大产能说明市场需求向好,是实力与产业有前景的证明,但如果没有政府前期的慧眼识珠,一切也无从谈起。
毫无疑问,几乎所有中西部城市都想复制宁德案例。那么,面对新兴产业如何提前研究并锁定种子,是当前政府招商引资最应聚焦的。
招大引强,成长性与忠诚度不高
只要抓住一个产业变迁窗口,城市就能快速实现能级跨越。
20年前,成都、重庆、郑州这些中西部城市正是抓住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梯度转移机遇,将英特尔、富士康、惠普、戴尔、联想等巨头的产线瓜分殆尽,GDP排名迅速上升。
于是招大引强成为这些年政府招商引资的信仰,各领域的500强名单几乎人手一册,为同一家公司争得头破血流。
但继续延续这种产业招引逻辑存在一些潜在问题。
其一,名花有主。上一轮产业迁移已告结束,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几个大产业的城市归属基本上尘埃落定。
其二,僧多粥少。大项目数量少容易引发恶性竞争,即便花费巨大成本成功引进,最后算总账或得不偿失。
其三,凤尾长不出凤头。中西部城市引进的大项目,大多是梯度转移的末端环节,横向变粗易,纵向长高难。
总体而言,过去中西部城市承接东南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实际上是沿海地区承接美日韩产业梯度转移的延伸,如深圳富士康、上海英特尔搬迁。
对比沿海,中西部城市存在人才吸引力不足和地理位置偏远难以融入国际分工等天然弱点。
很多中西部城市都存在一种现象:本土公司很难做大,但本土能人走出去,反而把公司做大了。
而且,中西部城市承接梯度转移的多是企业生产部门、代工厂等分支,引进的人才是职业经理人而非创业者,这些项目重度依赖总部规划,缺乏自我生长机制,一旦上面调整,说裁撤就裁撤。
这意味着,无论是内部能人支撑,还是外部环境刺激,都不足以令中西部城市在短期内从产业链底端爬升出国际一流公司。
即便是先进的东南地区亦如此。2010年富士康大举内迁,高峰期有40万人的深圳龙华富士康一时人心惶惶,配套企业蠢蠢欲动,南方都市报甚至发出了《富士康搬迁致产业链断裂 龙华科技城或将搁置》的报道,虽然后来龙华富士康并未如传言搬走,但着实给深圳敲了一记警钟。
今年3月,富士康宣布拟定增45亿人民币在越南建设工厂。目前,富士康估计已经约有30%-40%的产品线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而且这一比例可能还会上升,逐渐搬出中国预判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厢,员工最多时高达18万人的三星中国是实打实撤离了。2018年开始三星就相继关闭天津、惠州的手机工厂,2020年又关闭了位于苏州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
拥有强大供应链、交通信息网与高效政府服务的东南城市尚如此,中西部城市更要考虑梯度转移来的工厂流动风险。
相比而言,东南城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本土企业,实现了产业链升级,不惧工厂搬迁带来的空心化。但中西部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打回原形。
内生企业做大尚需时日,梯度转移企业的成长性与忠诚度又不高,那么,中西部城市如何基于本地特点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产业升级?
资源+科技,偏远新疆逆天改命
如果说宁德主要是占了天时地利的运气,那么新疆光伏的崛起则更多体现了人为布局的前瞻。
目前,新疆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石河子和奎屯、阿拉尔为两翼的硅材料、太阳能电池/组件封装、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制造业基地。
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我国多晶硅产能为49.5万吨/年,预计到2021年底,产能将达到54.4万吨/年,产能全球占比接近80%。其中,新疆约占全国产能57%,占据光伏上游的绝对领先地位。
科创板市值1300多亿,仅次于中芯国际排名第二的大全能源就是一家新疆公司,来自2011年招引的江苏项目,如今研发与制造都在新疆。
有意思的是,大全能源创始人徐广福与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都是江苏扬中人,无锡尚德破产,除了欧美双反市场需求萎缩,还在于硅料成本居高不下,徐广福在同乡跌倒的地方站了起来。
太阳能光伏硅料的纯度,要达到99.9999%以上;电子级硅料纯度,要达到99.9999999%以上。可见硅料生产,都是极致精细化的提纯过程。
这个环节具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和垄断性。在光伏硅料的基础上,大全能源打算进一步提纯进军电子级硅料,这是个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1997年提出来做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SiC)单晶,最早投资支持他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这个项目发展成天科合达半导体公司,今年入选国家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截至2020年底,新疆有59家A股上市公司,与陕西一样多,比重庆还多3家,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16居中游,作为一个西北偏远省份殊为不易。
2011年是中国光伏产业最惨淡的时期,新疆果断出手抄底,招引东部光伏企业赴疆过冬,与大全能源一同入疆的还有合盛集团、哥兰德新能源等一批当时的光伏知名企业。
新疆吸引光伏企业有其资源禀赋优势,新疆煤炭、风能、光能位居全国前列,相应有着较低的电力成本,工业用电价格低于内地价格的50%左右,在电力成本占35%的多晶硅生产上极具竞争力,新疆充足的电力供应能够保证晶硅低成本生产。
但是青海、内蒙古与西藏等地资源禀赋优势同样突出,电价与新疆相差无几。尤其是青海,除10千伏一般工商业用电,在居民生活用电与其他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上比新疆还低,为全国最低价。
中国光伏教父施正荣早在2006年就悄悄在青海布局多晶硅生产,是亚洲硅业的背后实控人。
据经济参考报2009年报道,当时业界的共识是,综合太阳能资源、土地资源、气象、电网、负荷、地理、交通及光伏产业链等各种因素,青海省的光伏利用整体条件在全国最优。
青海在2009年发布《青海省太阳能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规划(2009-2015年)》,其主政官员接受媒体采访认为,青海成为全国新能源产业老大指日可待。
不过今天来看,光伏产业的老大好像更有新疆味儿。
既然资源禀赋差不多,产业发展却结果迥异,倒推产业规划与执行,新疆或许做得更好。
2010年5月17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此次会议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是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路径选择,并给予新疆、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新疆在2012年发布了《新疆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对比青海新疆的产业规划,新疆对光伏产业认知更深刻,招商思路更清晰。
新疆明确形成“煤—电—硅—太阳能光伏集成应用”循环经济产业链,将资源禀赋优势充分发挥在光伏产业上游的硅料生产上面,而不是西北其他几个省份偏向光照优势注重终端光伏发电。
在缺乏特高压输送的前提下,西北省份光伏发电难以做到充分消纳。中电投黄河上游公司、中广核、保利协鑫、无锡尚德集团4家企业曾在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建有光伏电站,最后无奈地达成一项看来非常可笑的协议:轮流发电!没有轮到的电站,只好呆着“晒太阳”。
一般情况下,产业链的核心集中在上游原材料、关键元器件零部件与下游终端应用两头,而一个新兴产业的技术标准与终端市场需求处于变动之中,发展之初做强上游更重要。
比如,新疆的产业规划就在硅料生产方面做了周密测算。
“初步测算,多晶硅材料约占并网光伏发电系统成本的37%,而电力成本又占多晶硅成本的30%以上。若形成1万吨多晶硅加工产业链,就要消耗200万吨煤炭和近10万吨的石英岩矿。而1万吨多晶硅转化后产品的运输量仅相当于转化前资源运输量的1/200,可极大缓解新疆运输的“瓶颈”问题,是原子流向电子流转换、实现由“原字号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的一条战略路径,对加快实施资源转换战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新疆的光伏产业成为西部落后地区利用资源优势结合高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
康波周期,60年一遇
宁德和新疆两个案例发生在十年前,它们给了中西部城市一个启示:
面向新兴产业招商,正是中西部城市摆脱梯度转移的工厂流动风险,快速实现产业链升级的可行之道。
当下,科技发展使中西部城市面临的机遇更多。2021年,两大经济规律的周期循环叠加,催生了新兴产业爆发。
一是放眼世界,“康波周期”开启了新一轮循环。
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长周期变化,一个循环是60年,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甲子,分为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阶段,简称康波周期。
最初,康德拉季耶夫以重大经济危机作为划分依据,没有特定的宏观变量,为此争议很大。后来“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作为长波周期划分的根据,即不同的技术创新与不同的长波周期相互联系起来,这比重大危机的划分更加具有说服力。
人类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5次康波周期,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摩尔定律”接近极限,集成电路发展遇到瓶颈,美国的发展速度变缓的表现,成为本轮长波(第五波)繁荣向衰退转换的大拐点。
“信息技术爆发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国展开。当技术从主导国传导到中国,再扩散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作为本轮康波中的追赶人,这个技术在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这是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周金涛2016年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技术当它在追赶国的渗透程度达到了无孔不入的时候,一定到达了它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这个技术后面就是一个成熟并衰落的趋势。
的确如此,中国互联网这些年来的创新乏善可陈,不断倒腾各种商业模式做流量变现,以至于人民日报连发评论喊话巨头: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信息技术增长乏力也让全球呈现为存量争夺的内卷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国际环境的恶化,贸易战、科技战接踵而来。
很正常,老大跑不动了,就会伸腿绊老二。
不过新的一页即将翻开,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即将到来。
从1958年集成电路问世推动信息革命至今差不多60年,我们正在进入这一轮康波周期的萧条阶段,同时也意味着科技革命的转折点近在眼前。
二是观察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联动也开启了新一轮循环。
过去中国主要是吸收前面几次康波周期的技术,将其扩散到生产的各个领域,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并不明显,反而是以房地产、老基建为代表的城市化进程将汽车、家电等技术扩散出去,同时吸收供给过剩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
1998年中国启动房改加快城市化进程,1999年城市化率30.89%,2000年飙升到36.22%,此后逐年上涨,迎来20来年房地产业的高歌猛进,2021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3.89%,城市化进程趋缓,房地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疲软,进入“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与“新工业建立”的循环。
数据来源:邱晓华,“论世界制造业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2020年,国家提出新基建,加快5G网络、特高压、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建设进度。2021年,“十四五”规划强调诸多科技创新的新工业。
两个循环进入新的阶段,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叠加。
于是,我们看到商业模式创新转向硬核科技创新,互联网虚拟经济转向新工业实体经济,第四次科技革命呼之欲来,中西部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再次显现。
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新型制造业西迁
每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的制造业,点亮城市经济。
第一次科技革命革新了棉纺织业,让曼彻斯特成为世界棉都;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钢铁汽车业,崛起了底特律汽车城;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明了计算机集成电路,让硅谷成为延续至今的传奇。
第四次科技革命,表现为碳中和的能源变革与智能化的高端制造业。当前能源变革的制造业属性大于资源品属性,所以此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在前期就是高端制造业。
无论能量还是信息,都需要物质的载体,最终落到实体制造业头上。
如今硬科技成为热词,“硬”字除了代表技术过硬,还有一层硬件制造的含义。
尤其是在科技革命的伊始,更需要搭建硬件平台,才能在其之上长出软件生态。哪怕是互联网,也需要计算机与智能手机作为人机交互的硬件终端。
当移动互联网进入万物互联的AIoT(人工智能物联网)时代,所需的硬件终端将不再是手机一家独大。
第三代半导体与新一代模拟芯片制造、新型显示器件、新型通信基站、XR终端、智能机器人、商业航天、超级高铁、化学与生物创新药等等,这些新兴产业里其实蕴藏着很多成长中的“头雁”。
新能源变革也是棋到中局,接下来的氢能储能、固态电池等新技术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第一次光伏产业爆发,江苏无锡抓住了尚德电力,后来市场风云变幻,结果光伏产业被新疆抄了底。
只要不是演进到像消费电子与互联网这种成熟产业,各地都有机会争抢新兴产业的盛宴。
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高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从十三五规划的15%上升至17%。
相较十三五规划聚焦的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材料、新能源领域,十四五规划新添了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前瞻谋划未来产业方面,十四五规划新增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还将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到全新的历史高度,将科技自立自强发展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
同时,由于一线城市土地承载有限,成本高昂,上海深圳也在出现新型制造企业溢出现象。
上海整个“十三五”的新增产业用地只有25-30平方公里,2018年特斯拉在上海一次拿地就是0.8平方公里,已经堪称大手笔。
深圳更捉襟见肘,2018年城市共创大会上王石曾透露,经过四十年的开发,深圳现在可开发的面积只剩下20平方公里左右,每年新增用地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建设与土地利用“十三五”规划》
2019年深圳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显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599.7亿元,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95%。
报告还指出,近三年外迁的192家企业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共计27家,占全部外迁企业的37.5%。外迁企业已不止是传统低端制造业,而是延伸至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业。
深圳市总面积1997平方公里,在37个中国城市、副省级城市、特别行政区辖区中倒数第4,还不到苏州的1/4。
且因为丘陵地形,深圳一半面积被划入生态红线保护范围不得开发。为了力保制造业发展,这些年来深圳在剩下一半土地中坚守工业用地30%红线,不过这也导致深圳的住宅用地奇缺,造成今天深圳的房价超越北京上海,加重了制造业的用地成本,产生挤出效应。
2020年10月,史丹利百得精密制造(深圳)有限公司宣告解散,其称深圳工厂租期将于2021年到期,但因当地租金涨的过高,为了节省运营成本,所以不得不关闭深圳工厂。
深圳的企业搬迁潮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2016年,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就曾在讲话中表示,“近期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据科技部对国家高新区的2020年综合排名,深圳高新区仅次于北京、上海,但在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项排名第十,在成都、苏州、合肥等城市以后。
新型制造业爆发和一线城市的有限承载正在赋予中西部城市招商引资新的历史机遇。
中西部产业升级,从招引到招投
新型制造业西迁,与上一轮成熟制造业西迁,又不一样。
后者只看中成本优势,哪的地和劳动力便宜,就往哪里去。前者除了成本优势,还对当地人才供给、居住环境等提出了要求。
因为新型制造业不是简单的来料加工组装,研发制造一体化,制造工艺精细化,都需要高技术人才来执行。
梳理下来,中西部城市主要是成都、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贵阳等地具备的综合优势较为明显。
成都位于平原,环境宜居,有电子科大、川大、西南财大输送人才。重庆是西部之头、中部之尾,重工业发达。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继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之后,确定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战略地位。 武汉九省通衢,云集武大、华中科大、中南财经等高等院校。郑州占据交通枢纽,经济腹地广,近年发展很快。西安千年古都,西工大坐镇科研基础。贵阳敢为天下先,前几年大数据产业搞得风风火火。 总的来说,中西部城市各方面资源禀赋差距不大,谁能抓住新型制造业西迁的机会长出龙头企业,关键还是看企业招引能力。
成都位于平原,土地供给充足,环境宜居,同时也有电子科大、川大、西财等高校输送人才;武汉、重庆重工业发达,高等大学云集;郑州占据交通枢纽,近年发展很快;西安千年古都,西工大坐镇科研基础;贵阳敢为天下先,前几年大数据产业搞得风风火火。
总的来说,中西部城市各方面资源禀赋差距不大,谁能抓住新型制造业西迁的机会长出龙头企业,关键还是看企业招引能力。
地方政府招商,最早是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企业,有了产业基础之后发展到产业链招商,逐步将龙头企业招引进来,带来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进入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这是针对成熟产业的招商套路。
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既不完善,也没有明确的龙头企业,无论是宁德时代还是大全能源,都不是产业链招商带来的成果。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本土资源与高科技结合的产物。
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宁德的老乡资源,或者新疆得天独厚的煤电土地与光照资源,要将新兴产业的潜在头雁企业引来,通行办法之一是砸钱。
新兴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是个企业都缺钱,从产业链招商到资本招商,各地政府成立创投基金,从招引到招投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既要招大引强,争抢蛋糕;也要招精引新、投新做精,做大蛋糕。
中西部城市摆脱“厂妹”的宿命,在此一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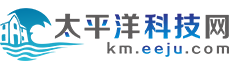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